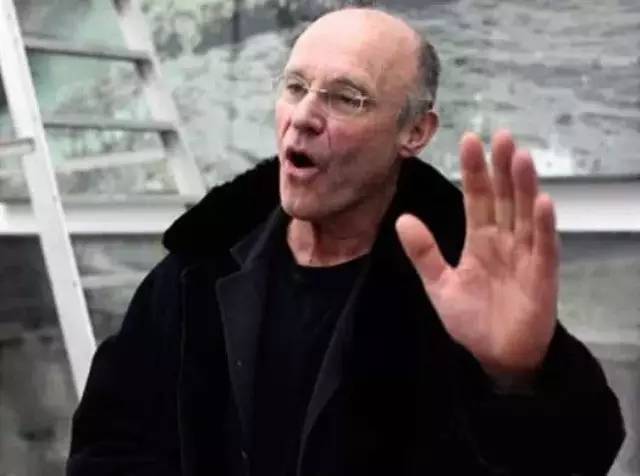安塞姆·基弗
2018-1-6 潮望艺术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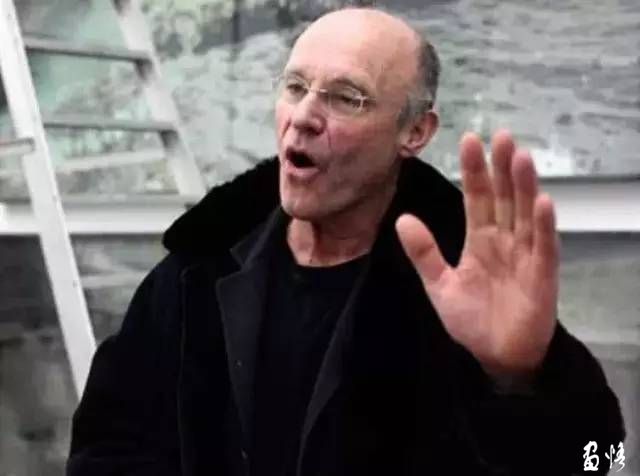
安塞姆·基弗(AnselmKiefer,1945-),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之一,德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和美术家。70年代,他曾师从德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前卫艺术家约瑟夫·波伊斯(Joseph Beuys)和Peter Dreher。基弗曾有“成长于第三帝国废墟之中的画界诗人”之称谓,其画无论创作手法还是呈现面貌均极为现代,但往往主题晦涩而富含诗意,隐含一种饱含痛苦与追索意味的历史感。

基弗的创作思想包含了他对民族性的探寻,他将他自身的历史当作一个有意义的创作源泉,并对整个过去岁月进行了反思与重组。在他的作品中,这些思想的很大部分是通过广袤、焦枯(他在奥登瓦尔德的画室周边地区)的自然景象来表现的,同时以一种恢弘、崇高的手法使之获得了新生。在这次访谈中,他对德国与再生的强调,他对神话主题的运用,以及他对美国艺术家的评点尤其具有启发性。
起初,作为一个观念艺术家,基弗于 1970年在卡尔斯鲁厄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。此后的1973年在科隆的迈克尔·维纳画廊;1977年在卡塞尔第六届文献展;1980年在威尼斯双年展,都展出了他的作品。1981年,在纽约的玛丽安·古德曼画廊,我们经人介绍认识了他。
这个访谈是根据1987年6月10日在弗里德里希安博物馆进行的一次非正式的、未录音的谈话整理的。基弗当时正在那里为德国卡塞尔第八届文献展安装他的作品。
起初,作为一个观念艺术家,基弗于 1970年在卡尔斯鲁厄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。此后的1973年在科隆的迈克尔·维纳画廊;1977年在卡塞尔第六届文献展;1980年在威尼斯双年展,都展出了他的作品。1981年,在纽约的玛丽安·古德曼画廊,我们经人介绍认识了他。
这个访谈是根据1987年6月10日在弗里德里希安博物馆进行的一次非正式的、未录音的谈话整理的。基弗当时正在那里为德国卡塞尔第八届文献展安装他的作品。

唐纳德·库斯皮特——简称DK,
安塞姆·基弗——简称AK。
DK:听说你总摆脱不了德国人的事情。显然,对你而言,他们不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事。但是你的一些作品中对海德格尔的描绘却充满了讽刺意味。
AK:是的,我对海德格尔的矛盾心理很感兴趣。他的著作我不太熟悉,但我知道他曾是个纳粹分子,像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被纳粹蒙骗了呢?海德格尔怎么会这样没有社会责任感了呢?还有塞利娜: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,却是个腐朽的排犹分子。这些看上去聪慧、明智、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,在社会问题上怎么会有这样愚昧而庸常的见解?
为了表现这个想法,我画了一个蘑菇状的肿瘤,从海德格尔的脑中长了出来。我想表现他思想中的矛盾——一切思想中的矛盾。“矛盾”是我所有作品的核心题材。
没有什么地方像德国这样到处充满了矛盾,即使是德国的思想家们也看出了这一点。比如,尼采和海涅,就以一种憎恨的心态表达过他们对德国矛盾的感受,他们都是德国人。这种矛盾尤其体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上,德国的犹太人,由于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,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矛盾性。与傲慢的德国理性相反,犹太人体现出一种道德感,我试图像海涅那样,既表现出德国人的理性又表现出犹太人的道德。
安塞姆·基弗——简称AK。
DK:听说你总摆脱不了德国人的事情。显然,对你而言,他们不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事。但是你的一些作品中对海德格尔的描绘却充满了讽刺意味。
AK:是的,我对海德格尔的矛盾心理很感兴趣。他的著作我不太熟悉,但我知道他曾是个纳粹分子,像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被纳粹蒙骗了呢?海德格尔怎么会这样没有社会责任感了呢?还有塞利娜: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,却是个腐朽的排犹分子。这些看上去聪慧、明智、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,在社会问题上怎么会有这样愚昧而庸常的见解?
为了表现这个想法,我画了一个蘑菇状的肿瘤,从海德格尔的脑中长了出来。我想表现他思想中的矛盾——一切思想中的矛盾。“矛盾”是我所有作品的核心题材。
没有什么地方像德国这样到处充满了矛盾,即使是德国的思想家们也看出了这一点。比如,尼采和海涅,就以一种憎恨的心态表达过他们对德国矛盾的感受,他们都是德国人。这种矛盾尤其体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上,德国的犹太人,由于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,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矛盾性。与傲慢的德国理性相反,犹太人体现出一种道德感,我试图像海涅那样,既表现出德国人的理性又表现出犹太人的道德。

(摄影:宋新郁)
DK:许多美国人认为你的作品很美,他们看不出其中的矛盾性,也看不出你在矛盾中找到了美。
AK:美国人总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。要对“美”作一番描述,对我来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。我曾为一件作品花费了5年的时间,单纯为了美似乎是不太值得花费这么些心思的。我想它还算是美的吧。
DK:阿多诺说过,在奥斯威辛之后,人们再也不可能写出抒情诗了。这个观点也许可以引申一下:在奥斯威辛之后,再也不可能有美的艺术了——那是一种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美。
AK:我相信艺术是有责任的,但它同时仍然应该是艺术。作为艺术,许多艺术种类都是卓有成效的。在当代,极少主义是个不错的例证。但这种“纯粹”的艺术有失去内容的危险,而艺术中应该是有内容的。我艺术的内容也许不是当代的,但它有政治色彩。它是一种积极行动者的艺术。

DK:许多美国人认为你的作品很美,他们看不出其中的矛盾性,也看不出你在矛盾中找到了美。
AK:美国人总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。要对“美”作一番描述,对我来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。我曾为一件作品花费了5年的时间,单纯为了美似乎是不太值得花费这么些心思的。我想它还算是美的吧。
DK:阿多诺说过,在奥斯威辛之后,人们再也不可能写出抒情诗了。这个观点也许可以引申一下:在奥斯威辛之后,再也不可能有美的艺术了——那是一种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美。
AK:我相信艺术是有责任的,但它同时仍然应该是艺术。作为艺术,许多艺术种类都是卓有成效的。在当代,极少主义是个不错的例证。但这种“纯粹”的艺术有失去内容的危险,而艺术中应该是有内容的。我艺术的内容也许不是当代的,但它有政治色彩。它是一种积极行动者的艺术。

DK:你创作过许多不同种类的作品,有没有哪种风格是你特别喜欢的?
AK:我最喜欢编书。但也喜欢环境艺术和行为艺术,单单绘画是很难完全实现我的想法的。从1969年起,我就在编书了,它们是我的第一选择。
DK:1987年5月在纽约玛丽安·古德曼画廊举办的展览中,你展出了一幅表现奥西里斯与伊希斯的作品,和一幅以核能量为主题的作品,它们面对面地挂着。从尺寸和笔法上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,但它们的联系一定还以其他方法表示出来。你是怎么使它们相融合的?
AK:我对精神力量和技术力量之间的关联是很感兴趣的,也许可以进一步称之为技术潜力和精神力量。这些作品间的物质上的关联,以这种方式最低限度地暗示出来:奥西里斯有14个片段,而核反应堆有14个杆,它们暗示出一种更深层的精神联系。伊希斯和奥西里斯的故事是关于再生的,而我认为核的主题也在于此。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,你也许记得,伊希斯找不到阴茎,核堆就是一种阴茎,这是对潜在的毁灭性力量的建设性运用,它充满了有关力量之再生的涵义。
AK:我最喜欢编书。但也喜欢环境艺术和行为艺术,单单绘画是很难完全实现我的想法的。从1969年起,我就在编书了,它们是我的第一选择。
DK:1987年5月在纽约玛丽安·古德曼画廊举办的展览中,你展出了一幅表现奥西里斯与伊希斯的作品,和一幅以核能量为主题的作品,它们面对面地挂着。从尺寸和笔法上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,但它们的联系一定还以其他方法表示出来。你是怎么使它们相融合的?
AK:我对精神力量和技术力量之间的关联是很感兴趣的,也许可以进一步称之为技术潜力和精神力量。这些作品间的物质上的关联,以这种方式最低限度地暗示出来:奥西里斯有14个片段,而核反应堆有14个杆,它们暗示出一种更深层的精神联系。伊希斯和奥西里斯的故事是关于再生的,而我认为核的主题也在于此。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,你也许记得,伊希斯找不到阴茎,核堆就是一种阴茎,这是对潜在的毁灭性力量的建设性运用,它充满了有关力量之再生的涵义。

DK:这也就是德国的再生吗?是关于德国的再统一吗?
AK:某种意义上是的,但“再生”并不一定意味着“再统一”。再生是一个政治性主题,但它还与更大的问题密切相关,这里面也包括艺术之再生的问题。
DK:你觉得在今天,艺术尤其需要再生吗?
AK:我想是的。为艺术而艺术(ars gratia artis)的东西已经太多了,它们提供不出多少精神食粮。艺术是非常具有乱伦性的:那是一种艺术对另一种艺术的反应,而不是对世界的思考。当它对艺术以外的事物作出反应,并且的确是出自某种深层需要时,就会处于最佳状态。
AK:某种意义上是的,但“再生”并不一定意味着“再统一”。再生是一个政治性主题,但它还与更大的问题密切相关,这里面也包括艺术之再生的问题。
DK:你觉得在今天,艺术尤其需要再生吗?
AK:我想是的。为艺术而艺术(ars gratia artis)的东西已经太多了,它们提供不出多少精神食粮。艺术是非常具有乱伦性的:那是一种艺术对另一种艺术的反应,而不是对世界的思考。当它对艺术以外的事物作出反应,并且的确是出自某种深层需要时,就会处于最佳状态。
DK:除了矛盾以外,你的艺术中还有其他思想吗?
AK:也许我最好这样说:我毫无理由地对一个诺斯替教派的思想家瓦伦蒂诺感兴趣,他认为这个世界形成于偶然间,也将在偶然间消逝。
DK: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你的作品中充满了绝望,而那种低调的色彩也就是绝望的阴影吗?
AK:我没有表现绝望。我对精神的净化总怀有希望,我的作品是精神的或理性的。我想在一个完整的环境中表现出精神与理性的契合。
波依斯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,他试图改变人类。我想表现出一些东西,然后表现出其可改变性。人们认为波依斯的作品是低调的,但这是一个误会,他向我们展现了真实,而这真实是生命的一部分。他让我们享受真实,他的艺术是令人愉快的。

(摄影:宋新郁)
DK:犹太人是你许多作品的共有主题,你能多谈一点你对他们的态度吗?对于德国人而言,犹太人怎么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主题呢?
AK: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得对德国做一些描述:二战后,德国到了紧急关头,关于它自己的神话已经破灭了。甚至它本身也不再有真实的存在。从那以后,德国变得比以往更加自力更生,也更世界主义。而犹太人,有史以来就被迫成了世界主义者,对德国人来说,他们是前车之鉴。他们在艺术上也是世界主义的,比如说,大多数收藏家都是犹太人,看来他们也知道我的艺术,当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,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,这些和新的、世界主义的德国有很大关系。
DK:但很多人认为你是个古老、排外、神话般的德国的怀旧者。
AK:我不是怀旧,我只是试图记住这些。
DK:我想,也许我们可以谈谈美国艺术,有让你感兴趣的美国艺术家吗?例如,对于与你完全背道而驰的沃霍尔,你是怎么看的?
AK:他很有趣,因为他表现了社会上的矫揉造作和垃圾般的东西。虽然他表现的都是表面化的事物,但他非常理智,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逻辑学家,他给表面化的东西以深刻的意义,而那正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能做的。我比较喜欢纽曼,他和流行文化保持了更多的距离,解释它,而不是随波逐流。我也许更能和莱曼、罗斯科产生共鸣。我也喜欢奥尔。对于极少艺术,我总的来说是比较赞赏的,以为它卸掉了一切历史的包袱,但它看上去并不完善。我喜欢有个人立场的艺术家,比如马塔·克拉克,他的作品和我很相像,是一种考古插图。

DK:马塔·克拉克的作品是昙花一现,仅仅存留于文件中。有些人认为你的作品十分脆弱,可能不易留存下去。
AK:我对物质意义上的存留不感兴趣,它的最主要精神将以其他方式存留下来。一个人可能创造的是永恒,却一度被忘记,但它表现出的无法承受的思想将使它被记住。许多作品都是单薄的,但其中的张力却被留存下来,比如立体派的作品,波洛克、劳森伯格的作品。我处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紧张压力的方式将存留下来,就像在保罗·塞兰的诗中一样,它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我很相似。
DK:你写过关于你自己的文章吗?
AK:写过很多,但都不正式,算是个人的自我戒律吧。
AK:我对物质意义上的存留不感兴趣,它的最主要精神将以其他方式存留下来。一个人可能创造的是永恒,却一度被忘记,但它表现出的无法承受的思想将使它被记住。许多作品都是单薄的,但其中的张力却被留存下来,比如立体派的作品,波洛克、劳森伯格的作品。我处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紧张压力的方式将存留下来,就像在保罗·塞兰的诗中一样,它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我很相似。
DK:你写过关于你自己的文章吗?
AK:写过很多,但都不正式,算是个人的自我戒律吧。

(摄影:宋新郁)
DK:你似乎对于你艺术中有关历史性的需要很有见地。
AK:我以为它使得极少主义与观念艺术更完善。它是不是绘画并不重要,风格、媒介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思想。
DK:那么你认为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思想家吗?
AK:艺术家有三个维度:意志、时间、空间。在美国,人们将艺术家当作一个物品制造者,但艺术不是物品,艺术是一种获取的途径,充满了考古学的潜在意义。
DK:你和其他德国艺术家有什么联系吗?
DK:你似乎对于你艺术中有关历史性的需要很有见地。
AK:我以为它使得极少主义与观念艺术更完善。它是不是绘画并不重要,风格、媒介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思想。
DK:那么你认为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思想家吗?
AK:艺术家有三个维度:意志、时间、空间。在美国,人们将艺术家当作一个物品制造者,但艺术不是物品,艺术是一种获取的途径,充满了考古学的潜在意义。
DK:你和其他德国艺术家有什么联系吗?
AK:没什么联系。我不是联系着的,而是孤立的。巴塞利兹买过我早先的一些作品,我也一度和迈克尔·维纳一起办过展览,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
DK:这种孤立有助于你的思想吗?
AK:它帮助我保持了思想、感觉、意志的统一性,我试图在一件作品中将它们综合起来。这种统一性才是真正需要的,而伊希斯和奥西里斯不过是名号而已,只是被武断地用来帮助那些想理解它们的人们理解他们。即使不知道那个神话,人们一样可以了解我作品的意义。

DK:你的德国人故事也是这样吗?
AK:它们更多的是因其涵义,而不是趣味而存在。我希望这些涵义能成为绘画之“物性”的对立面。比方说,“德意志民族的时代精神”( Deutschlands Geistenshelden)是毫无意义的,这种名字和作品的物性是矛盾的,这就形成了一种反讽,一种清晰的距离。这使作品显得晦涩,保证它不被立即“消费”掉,也不会轻易地为人所熟悉。即使我的标题会导致误解。我也不介意,因为误解创造距离,一个题目就如同讲演者放在他自己和公众之间的一本书,讲演和书并没有关系,但书却在讲演者和公众之间创造了一种反讽性的距离。

AK:它们更多的是因其涵义,而不是趣味而存在。我希望这些涵义能成为绘画之“物性”的对立面。比方说,“德意志民族的时代精神”( Deutschlands Geistenshelden)是毫无意义的,这种名字和作品的物性是矛盾的,这就形成了一种反讽,一种清晰的距离。这使作品显得晦涩,保证它不被立即“消费”掉,也不会轻易地为人所熟悉。即使我的标题会导致误解。我也不介意,因为误解创造距离,一个题目就如同讲演者放在他自己和公众之间的一本书,讲演和书并没有关系,但书却在讲演者和公众之间创造了一种反讽性的距离。

DK:你的反讽是和你的诺斯替教相联系的吗?
AK:就某种意义而言是的。诺斯替教的主旨是去感觉那不可知之物,那光。这个世界是从不可知之物中诞生的,也仍然保持着某种不可知的意味。光变成了物质,最后,火花将被聚焦于命运之轮上,又复归于黑暗的怀抱。
AK:就某种意义而言是的。诺斯替教的主旨是去感觉那不可知之物,那光。这个世界是从不可知之物中诞生的,也仍然保持着某种不可知的意味。光变成了物质,最后,火花将被聚焦于命运之轮上,又复归于黑暗的怀抱。

(来源:摘自《国际当代艺术家访谈录》)
阅读(6534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