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命的舒展与顽强
2021-11-11 宋群官网

在靖边,一种生长得有些奇怪的树,引起了我的注意,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,才知道它叫砍头柳。
这个有些壮烈的名字,让我的心,隐隐地痛了一下。
说它奇怪,还真是奇怪。一般的树,都顶着个大大的树冠,而砍头柳则是在它生长的过程中,在中间部分被拦腰切断,随后在被切断的地方,又生出许多个枝杈,这些枝杈,直直的甚至有些突兀的奔向天空。
在这些长长的枝杈上面,也都顶着个小树冠,晃动的叶子仿佛在说;不就是树冠吗?咱也有。顽皮的它们,像是戴了个翠色花环。
砍头柳的官名叫旱柳,当地人管它叫砍头柳。这一带的旱柳比较好活,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更有着一种随遇而安的品性。或许改造砍头柳,也是西北人智慧的一种选择吧,因为被改造后的砍头柳,会有更多的利用价值。于是,这些枝干长上几年,待有胳膊那么粗的时候,便可砍下来用做盖房子的椽子,或用来搭桥或做些农具。一些短的细小的,可以扎篱笆或者用来生火烧饭。
一排排旱柳,在眼前晃动,恍惚间,直觉得这些树,是老家门口那些伴我玩耍陪我长大的柳树。虽然它们在相貌上有所不同,没那么完整,或者说有些怪异不那么好看,可它们同样鲜活,同样质朴中带着灵气,同样会和着风儿,吟唱着那些我能听得懂的歌谣。
世间的每一种植物,都有着它的价值,砍头柳也是如此。
名字有些悲壮砍头柳,也不缺少柔情的一面。它会让春风,把它的花环染上绿色,然后美滋滋的第一个向人们报告春的讯息;它会拼尽全力的生长,尽可能的去做些有用之材;它也会身披晚霞,向辛劳了一天的人们招手致意。在它们看来,只要有雨露的滋润,只要有阳光的照耀,只要有星月的陪伴,足矣。
离我不远的地方,几个孩子正兴高采烈地跳着皮筋儿。她们把两端的皮筋儿,分别拴在了砍头柳上,她们似乎从没有察觉到砍头柳的特别,更没有觉得它丑陋。因为从她们出生,到她们长大,砍头柳就站在这里,她们已经习惯了它的样貌与陪伴。在她们眼里,砍头柳是善良而温情的,更是一个很好的玩伴。这些树给予她们更多的是陪伴,这份朴素,也只为陪伴。
就是这些砍头柳啊,在这里一站就是千年,站成了一段历史,站成了一道风景。我想象着,这个充满红色意味的靖边,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这些顽强的砍头柳,也会是战士们其中的一员。这方大雁高歌下的天空,是你和战士们的拼尽全力,才换来了今天的岁月静好。那时候的你,树冠还在,因为你要冲在前面,你要做将士们的掩体。
大漠孤烟,长风冷月,一颗颗顽强不屈的砍头柳,充满了牺牲,也充满了荣光。
砍头柳啊,如果要我给你起个名字,我会叫你重生柳。
你重生的样子很好看,遒劲的枝干,似一笔笔苍劲有力的线条,彰显着生命的蓬勃与顽强。虽干旱风沙狂风侵蚀,但只要有一点点沙土,只要有一点点泉水,你就能活。逆光中,你小小的叶子深沉而明亮,透露出一种坚韧无比的生命状态。
曾经有人比喻砍头柳“是一种壮烈的树,一种蓬勃向上的树,一种不断再生,不断舍身为人的树。”是啊,这就是你重生的模样,这就是你最美的画像。
你不去计较人们为你做了什么,你或许会对现在的有所作为而感到欢喜;为年复一年的生生不息而乐此不疲。你不是无根的浮萍,你会用力的把根须深扎在土里,虽然没有轰轰烈烈,却以你特有的姿态,诠释了生命的舒展与顽强。
也许,砍头柳的生长,有着一种疼痛,可这种疼痛却带给它另外一种美感。骨感的线条,呈现的是一种阳刚之美,一种力量之美,一种从容之美。也应了明代杨慎的诗句:“垂杨垂柳管芳年,飞絮飞花媚远天”。
有泪有歌的砍头柳,从不慌张。在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安静的生活。有着淡淡的优雅,亦有着动人的婆娑。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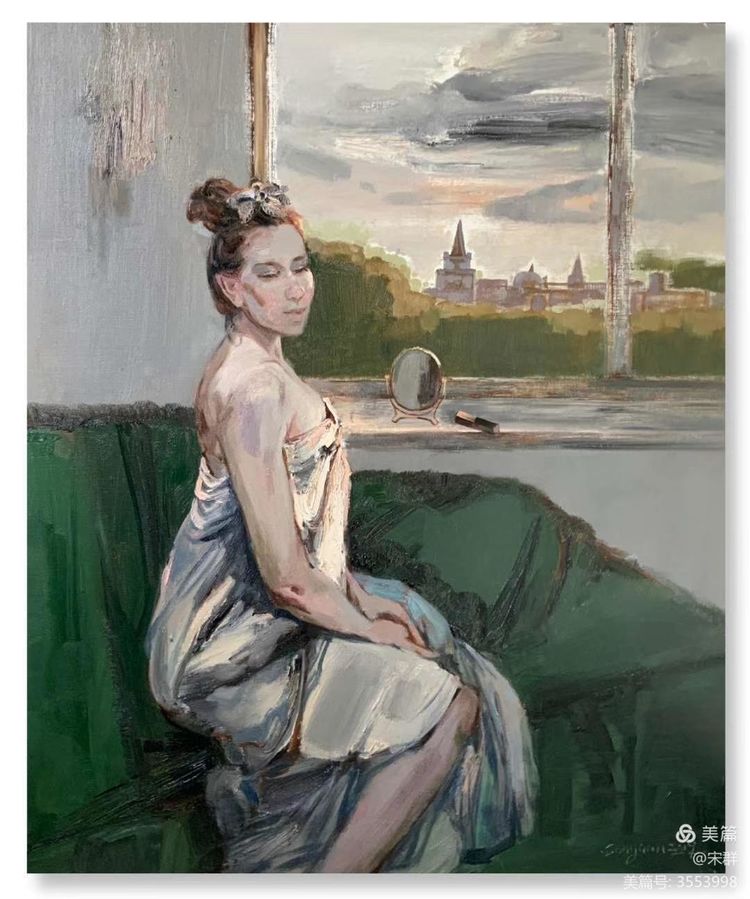





免责声明:以上信息为瀚望号发布,不代表瀚望艺术网观点。
更多内容
阅读 2190





